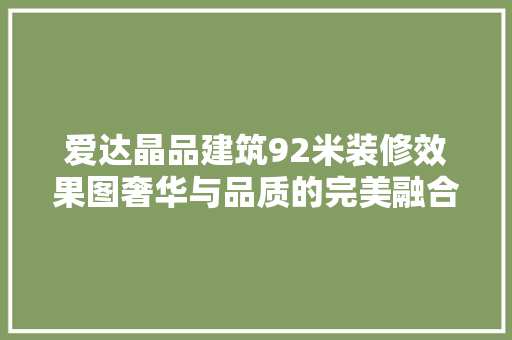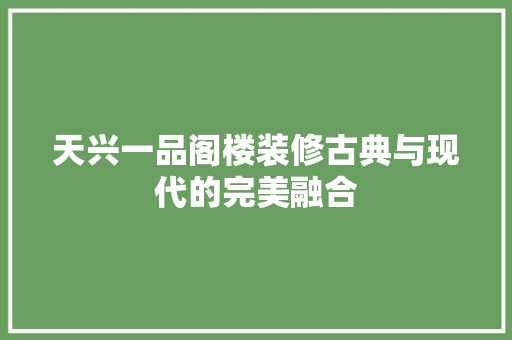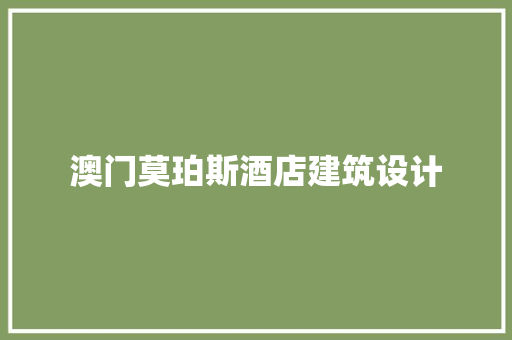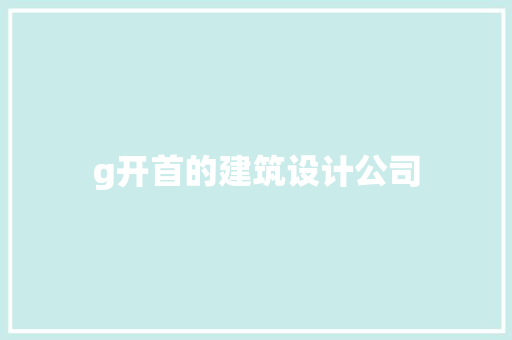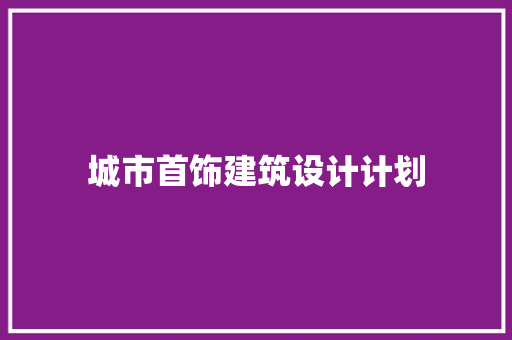目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公开搜聚见地。除了扩大保护工具、夯实保护任务等新哀求,《条例》中“历史建筑可以转让、出租”这一新提法,引发了关于“历史建筑该当怎么保护”的谈论。
乍一看,“转让”“出租”等字眼彷佛和“保护”背道而驰。但就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而言,保护和利用实质上并不冲突。过度开拓、大拆大造,显然不可取。反之,“铁将军把门”,则可能导致管理缺位,终极落得残破凋敝。从现实来看,历史建筑是分级管理的。有的确实不能“用”,但还是得“护”好。而更多的则是可以“用”的,那就要在“用好”中“护好”。诚如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所言,“保护古建筑不是要长期封闭,而是正常利用、修缮,它才会康健。”作为古都,北京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建筑遗存。这也决定了保护利用须要耗费大量资源,借助“市场之手”盘活社会力量,无疑是务实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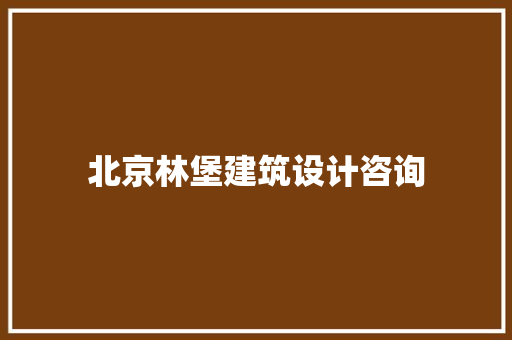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冻结式”保护行不通,很大程度在于将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割裂开了。放眼天下,实在很多历史建筑都在合理利用中抖擞时期光彩。比如荷兰林堡省一座建于14世纪中叶的教堂,被改造为一个远近有名的当代书店。斑驳的教堂穹顶壁画与当代图书、音像制品并存,给游客带来了奇妙体验。北京近些年也进行了探索,万松老人塔经由修缮,以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实体书店“多重身份”对外开放,不到400平方米的院落每天吸引着上千人次前来参不雅观。可见,历史建筑所承载的代价并非只属于“过去时”,它们也能很好地“活”在城市更新之中。让历史建筑与当代生活实现相互养活,不仅能拉近与民众的亲近感,夯实遗产保护的群众根本,也能获取更多社会资源反哺保护事情。
当然,历史建筑可以转让、出租,并不虞味着放低利用门槛,反而是提出了更高哀求。一方面,利用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干系的开拓必须建立在科学、详细的规范之上,绝不是天马行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消弭历史建筑的厚重感与文化味。对此,《条例》中给出了一系列“底线”“边界”。另一方面,历史建筑有其公共属性,开拓利用不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尤其是眼下,不少老建筑还在发挥着居住功能。因而保护利用的过程中,要优先考虑居民需求、公共做事等,在唤醒历史影象的同时,留住城市的文化乡愁。
在国际上,可持续发展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文化遗产的主要标准。让历史建筑融入城市发展,在人间烟火的浸润中抖擞出新的活气,这种保护才是真正对社会有益的,也才是可持续的。(晁星)
任务编辑: 马若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