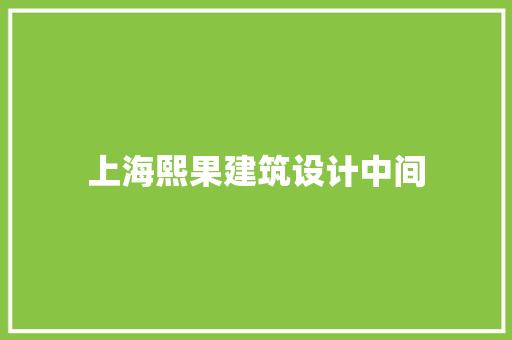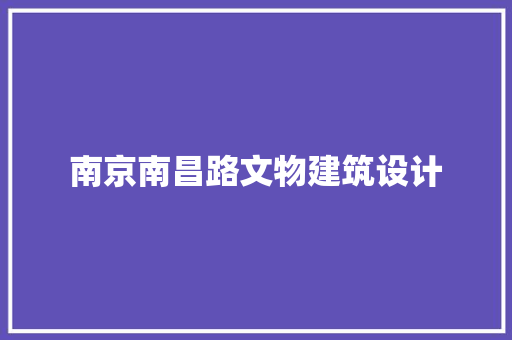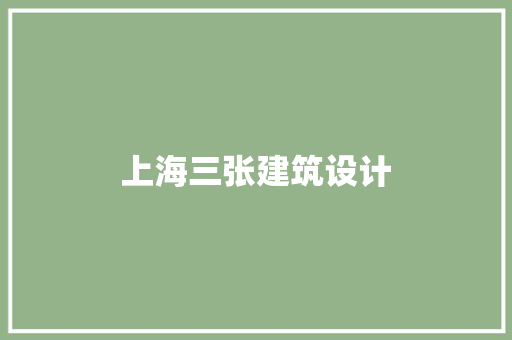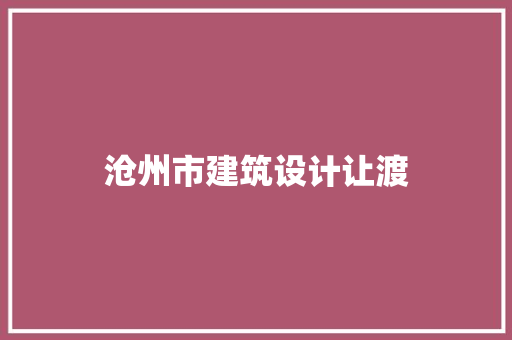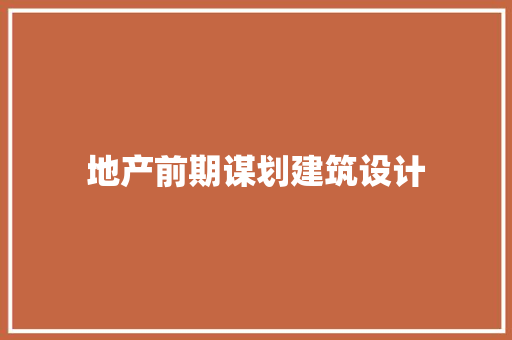1992年9月,
那是一个“伟大春天”后的金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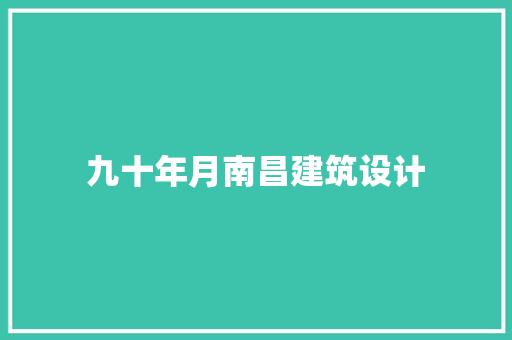
我告别学生时期,开始步入职场。
托邓大人南巡讲话后,
“胆子更大点,步子更快点”的福,
当年南昌所谓的好单位于是都“放开手脚,大肆扩招”。我们那几届毕业生当年事情分配的整体都比较好。
我分配的单位全称中国房地产开拓集团南昌公司(前身为南昌市公民政府统一住房培植办公室),这名字一听就金光灿灿,高大上。属当时市政府直属的奇迹单位(奇迹体例、企业管理),简称“中房”。
从前南昌的上海路小区、青山湖小区、鲤州小区、朝阳小区、新世纪小区以及沿江路等大片小区都是我们公司开拓的。
虽然历经多次的外立面“涂脂抹粉”,现在已是范例的老旧小区。
公司总部位于原经济大楼5楼整层。
经济大楼最初(现在的新东方豪景花园酒店)也是我们公司为市政府开拓代建的。
当年总公司旗下各个开拓处、名目繁多的经济实体、外地分公司、以及所谓外商互助的公司,加起来就有几十家,北京还有个“银河宾馆”,公司架构弘大,职员浩瀚,类似现今的许多政府的平台公司。
正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时胆大的辞去公职,直接“下海”;
稳健一点就想来到我们这种系统编制比较活、效益又好的公司。于是政府许多原来公务员体系的人都各显神通,找关系调进我们公司。
在那个大时期的背景下,
许多人的命运就此发生重大改变。
九十年代初,商品房市场已经涌现了,
但改革还是摸着浅滩的鹅卵石。
我们和市政工程开拓公司
(市政控股集团的前身之一)是南昌当时最大的两家国家一级开拓资质企业。
而当年中房彷佛不太瞧得起“市政”,
以为他们“土里吧唧,胆子太小,
思想不解放”。影象中市政当年只开拓了个现在的“桃苑小区”。
听说当年参评全国精良住宅示范小区时,
培植部考评组只瞄了几眼,便问陪同职员:“南昌还有别的小区看嘛”?
可凭心而论,桃苑小区在九十年代可谓南昌住宅小区的“颜值担当”。
科瑞集团郑跃文的“第一桶金”,
便是帮我们公司开拓的上海路新世纪小区发行债券赚到的。
三十年前,就懂得或者敢于考试测验发行地产开拓债券,可见当年我们领导“达老板”经营理念还是比较前辈前卫的。
后来我也逐步理解到,公司的很多职工家里都有些背景,涵盖了险些省市培植口干系单位领导的子女和家属。
“但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中房”早已是过眼云烟。
而同时起身,辈分相同的“市政”早已高歌年夜进,进化成为千亿级企业集团。
PART二: 中房设计所新来的年轻人
有点像部队新兵连,
我们刚分来的年轻人只假如建筑、工民建、给排水等干系专业的,总公司统一安排我们先去下属的建筑设计所磨炼,再做二次分配。于是小小的设计所一下子就来了10多个年轻人,叽叽喳喳,非常热闹。
【中房设计所】
位于珠宝街与童子路交汇的地方,这一带是南昌“钵子汤”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老左杂酱面就在对面的巷子里,刚刚开起;
象山南路春光绸布店旁还有那家著名的卖上海煎包和咖喱汤的“新园阁”
(现搬到嫁妆街);
附近高桥“洋船头”那时还开了一溜味道奇鲜的水饺店。这些旁边临近的老南昌美食,对付“吃货”的我至今还非常怀念。
我们这些年轻人中又以“江工”
(当时叫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的人居多。当年我以为自己还是个“菜鸟”,觉得他们大多已显老练成熟。这应证了当年南昌关于各高校有名的顺口溜:“江大的伪君子、江工的二流子、师大的舞棍子、财大的情种子”。
九十年代初,南昌已经开始大拆大建,
所里效益比较好,设计单位又都是有提成的,以是每月收入加起来在当时还挺高,中午吃落成作餐,老板一桌,我们几桌,还能打打麻将,日子过得很舒爽。
当年盛行的顺口溜是“十亿公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社会开始“统统向钱看”。
这种风气自然弥漫到我们这个本身许多同事家庭社会关系就比较繁芜的单位。
加上南昌正处在大培植的井喷阶段,建材短缺,于是我们所里几个生动的年轻人就考试测验做起了“掮客”的角色,“你有钢材吗,我屋里搞得到水泥哎,”类似这种建材中介的对话就常在所里的年轻人中生动地展开(但实在由于金额较大,中间人太多,他们实际成功率都极低)。
“有样学样””,我也迅速进入角色,
打起摩丝,夹上公函包。父亲老笑我:“人尺巴子高,每天夹个公函包”。
PART三: 第一次打仗地产发卖
我本来就对每天专一画图、
算钢筋的构造设计没有兴趣。
于是在总公司成立中房信息咨询中央
这个子公司,开启自身开拓项目发卖和二手房业务时,就自告奋勇,找到他们老总,自我介绍。
老总姓陆,是个女强人,很有眼力和思路,
实行力又强,我非常佩服她。
这个在1994年就成立的
一、二手房联动的房地产代理发卖公司,
在当时已经非常超前了。
办公的地点在滕王阁大门口南边的公司总部一楼(现已拆迁成广场)。由于常常近间隔看到外地游客在门口集体合影,公司的那些老油子嘴比较毒,常开玩笑,“快看,快看,猴子全体凑集”。
这是当年一些南昌人的恶习。
公司代理发卖的第一个项目便是作为总部大楼副楼的六套住宅。
我记得很清楚的缘故原由在于,
当时全体南昌的房价还在1000元旁边的时候,我们总公司的“老总”就把这几套屋子定价3000元一个平方。
他的情由很自傲:一是产品稀缺(全体南昌当时险些没有四房两厅两卫、150平米的商品房出售)、二是地段离滕王阁最近。三是数量便是六套,也是稀缺,肯定有那种顶级客户会买单,而价格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我们当时都以为价格高的实在太离谱,
但事实证明,老板是对的,
贫穷限定了我们的想象,
有钱人便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其实在我们之前,福州路口腔医院旁,南昌就出身了第一家非常牛B的房产中介公司,全称为南昌房地产咨询做事有限公司。
那个公司“出世即顶峰”。
90年代初,他们员工就统一制服,配了胸牌,尤其在员工的条记本上印有个人名字和公司LOGO,在那个时期给人觉得特殊规范和时尚。
后来听说这家公司老板赢利后在上海炒期货破产。如今这个南昌当地盘产中介的“祖师爷”,早已被人遗忘。
“罗志忠”从前彷佛也在这个公司待过,
后去了上海,90年代末回来时,做了鄢建华开拓的,南昌第一个引入当代房地产营销观点的“远东世纪花园”的第一任营销总监,他在南昌本土的地产营销界,资格极老。
“宁晓峰”便是我们老板从那家公司“挖”来的,我也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中介“下药”的专业暗语:中介公司通过发布一些根本不存在、性价比极高的房源来吸引客户咨询,从而获取客户资源。这种套路延续到本日都习认为常,屡试不爽。
宁晓峰后来对我影响很大,
他是南昌本土最早一批做房地产代理中介的,读研后去了深圳,做过老牌上市房企“深深房”的营销总监,后来是路劲地产(收购孙宏斌顺驰的喷鼻香港公司)的高管。
过去每次我到深圳,他回南昌,我们总会长聊一番。我初次打仗地产发卖他是我的老师,我后来考研也是受他的直接影响。
发展的旅途中大多数人仅仅只是遇见,
他们曾经从你的天下走过;
而有些人和事却改变了你生活的轨迹,
影响了你生命的韶光线。
我一贯以为宁晓峰改变了我的韶光线。
PART四: 南昌第一轮房地产开拓热潮
1992年,全体东京地价可以买下美国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这一年前后,南昌郊区“四小龙”(顺外、热心、湖坊、进顺)相继雄赳赳,气昂昂地迈进全国“亿元村落”的行列。
也正是在1992年,房改全面启动。
南昌开始了第一轮的房地产开拓热潮。
但当时房地产开拓还未对民营企业放开,
在此背景下,
许多市政府下面区、局级单位,溘然冒出了近百家以计委、经委、教委、旅游、华侨、东湖、西湖、郊区、湾里等单位为举头的各种“红顶”房地产开拓公司。
缘故原由很大略,
这些区、局级单位下面都有遍布南昌各个角落,原来属于国家划拨的“一亩三分地”,有些还是老城最核心的地块。
那时地皮市场都是协议出让,
而这些公司每每都没有什么开拓履历,但合法的“壳”,又有稀缺的市中央地皮资源,这让很多社会上的“能人”迅速嗅到了发财的机会,于是纷纭各显神通,搭上关系,借壳互助经营。
为此“鱼龙殽杂,乱象丛生”,
南昌房地产进入最早期的“春秋时期”。
九十年代,南昌传统老城区绝不夸年夜的是:
以广场为中央骑个自行车,
往周边四个方向蹬上不敷半小时,
不是骑到河里去,便是肯定能见到菜地。
红谷滩还是滩涂河汊,
“过八一桥”还是骂人的鄙谚。
现在南昌市老城区所谓的“握手楼”,
以及最高八层的多层建筑大多为那个时期的产物。后来普遍的封闭性社区、人车分流、物业管理、景不雅观配套等那时险些都不存在。
户型设计上什么动静分开,干湿分离,
明厨明卫那还是下个世纪的产品。
房地产开拓也根本没有什么营销策划的观点,广告推广的意识也不存在。
都是开拓商在工地上的办公室放个桌子,
图纸出来就卖房,很多老板自己便是发卖经理,司帐、出纳充当售楼员。
也没有按揭的政策,都是一次性付款(当然也根据进度分期)。
南昌房价在全体九十年代,
长期徘徊在1000-1500元之间,
险些都是自住或者改进,“炒店面已”经兴起,但“炒房客”,听都没听说过。
在当时“胆子更大点,步子更快点”思潮引领下,领导对我们“达总”也公开表态:
“现在是市场经济,不管若何,谁有本事把别人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谁就行”。
于是乎,言传身教,
公司的“门户”就此更加全面开放。
我们“中房”是房地产一级开拓资质、市政府直属企业的金字招牌,加上一些减免的规费(市政府常常从我们公司调拨一些商品房,分配给其它单位,以日后的开拓规费冲抵房款)自然吸引了许多“大项目”的“挂靠”。
而公司也乐得收取一定数量的挂靠费,
反正谁能赢利谁就行,哪管今后“大水滔天”,这也为我们公司后期的倒闭埋下了祸胎。后几任领导都疲于办理层出不穷的烂尾、质量、违约、上访等问题。
一韶光南昌中山路、胜利路、象山路、童子路、金盘路、站前路、提高路、井冈山大道、二七路上等黄金地段和老城区涌现了大批我们公司自己或者挂靠开拓的项目。
到90年代后期,
在中国房地家当真正走向市场化的前夜,
正准备拉开更加波澜壮阔的时期大幕时,
我们公司却深陷债务泥潭,
各种法律轇轕,濒临倒闭。
PART五: 九十年代南昌地产界的枭雄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义务,
也或许有其一定的宿命。
九十年代,在南昌房地产界:
王平(王森林)、王金林兄弟俩,
邓毛、“地主和唐老鸭”(陈桂林、唐卫华),晏广保、李建平,赵小平、赵平两兄弟等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
王平、王金林兄弟俩
项目多在中山路、胜利路与象山路的黄金地段(如胜利路上的金麟大厦、象山南路爱国电影院周边、杨家厂等);
邓毛的项目紧张在:
中山路、童子路(比如现在中山路的动壹基地、童子路的原抚州大厦);
陈桂林的开拓以三星大厦为标志,当年提高路与绳金塔周边的很多项目都是他们开拓。
李建平紧张为金阳光大厦、金昌利以及和其他人互助的开拓项目;
晏广保在开拓千禧颐和园之前,九十年代初就开拓了阳明路上的贤士花园。
赵小平最初是广场新华书店的地下商业改造项目,他更出名的是他开办的“清闲轩”。
弟弟赵平先是开拓了抚河桥的新田绿洲;
2000年前后,与张志宏互助了青山湖的碧海云天,在萍乡还做了几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项目,他是那个时期为数不多还在地产界基业长青的。
进入2000年后,在我们“中房”沦为倒闭的命运时,这些当年在南昌地产界气吞山河的人物也相继消逝在历史曾经给他们的舞台。
邓毛已过世,
湾里的“帝景湾洋城”,现在这类不太有名的项目,很多人都无法遐想到,开拓商曾是九十年代南昌房地产界的老大。
“唐老鸭”(唐卫华)当年在圈中长袖善舞,能说会道,彷佛后来是与胡智波(力推江西画坛十老,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合搞了站前西路的古玩城。
这些人在特定的历史年代,
凭着聪明胆大,野蛮成长,
捉住了历史给予的机遇。
他们血液里大概一定流淌着贩子天性对财富的狼性追逐,但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的局限,使得他们错失落了南昌房地产后期长达二十年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们在南昌地产界,
起身最早,收工也早。
PART六: “徐工”岁月
我在公司下属房地产咨询中央
那里待的韶光很短,继而又去了总公司的质检科,后改叫工程部。
虽然我对发卖很感兴趣,
但那时毕竟年轻,觉得能去公司总部事情,面子上更光鲜些,而且也想打仗下工地,当然更有我骨子里从不喜好按部就班的生活,性情始终“好动”,爱“折腾”有关。
于是95年旁边,我开始了被别人叫我“徐工”的监工地时期。
我们质检科的首任领导
是从市质监站调过来的“老江湖”,
他当时骑着辆时髦的摩托,眼神中透着自傲和诡秘,穿梭在各个工地上,显得非常神气。他的业务能力当时很让我佩服,下工地检讨走了一圈,瞄了几眼,就能说出十多条整改见地。
碰到做的很差,又喜好辩白的,
就会笑眯眯的戏谑包工头,“做了几年工地啊”,老板没听出来画外音,立时昂首骄傲的表白,“做了几十年哎”。“几十年啊!
做塌了几栋屋子哦?做成这样,赶紧跟我改”。
脸上的笑颜瞬间消逝。
下去检讨,用饭是当然的,
他总是轻松但又语气武断的随口一说,
听说哪里哪里刚开张,买卖很好,就到那里去尝下吧。
我一听就偷着窃笑,
他随口轻松说的都是南昌当时最好的几家高档酒店什么远东、华龙、金鹏、爱乐音等,包工头只有强颜欢笑,连说“好好好”。
我们虽说管的项目有几十个,
但多数实在是挂靠项目,下面还有分公司详细管现场的,作为总公司的工程质检部门,实际上权利职责并不大,但毕竟扛着总公司的大招牌。
每逢遇上大检讨或验收时,
那些抚州包工头总是要在脸上堆出笑颜站在工地门口,手上夹条红塔山,内心痛楚却还要摆出热烈欢迎的姿态迎候我们。
这些都让我颇为感慨,
包工头虽表面光鲜,但背后的酸楚,只有自己“独饮”,而且拖欠工程款在那时就已经很普遍,这碗饭真的不好吃。
当年在公司总部,人浮于事,
实际上,除了遇上市里的大检讨、省里、部里的抽检,去不去工地没人管你,想混日子很随意马虎。与后来我在民企比较,也从来没有所谓“996”的加班观点,大多数韶光,公司的年轻人一到中午,每每聚在一起打那时非常盛行的“六团”。
我一向少年老成,情商较高,颇得历任领导关照,有时还随着领导,与南昌从前的地产风云人物推杯换盏,有过场面上的打仗。
按世俗的理解,小日子过得蛮洒脱。
但我却越来越感到危急和发虚。
同学许多在工地现场虽条件艰巨,但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独挡一壁,而我自己觉得什么也没学到,去工地也就知道点皮毛,什么平整度、砂浆饱和度、钢筋外露等浅近知识,安乐光阴,我已感到了出息的隐忧。
尤其在那些所谓场面、酒桌的打仗中感触更深,太多的虚情假意,喝的时候称兄道弟,领导、领导,一旦用不着时,又形同陌路。
对此使我还落下一个“病根”,日后对付酒桌场面上与陌生人的应酬有些抵触,不愿多说话,更不愿去学酒桌上那一套所谓“得转”。
1996年,“达总”以及另两位老总的溘然退休成为调研员,让我本来便是一潭“活水”的内心,更掀波澜。
记得第一天调度任命刚下,
第二天三个同时退休的老总
就安排挤在厕所对面,一个险些最小的房间作为调研员办公室。
昨天“达老板”还在公司“呼风唤雨”,
随后的日子彷佛有一道无形的“潜规则的墙”拦住了他再踏进公司大楼的身影。
虽然我知道这是系统编制内的常态,
但年轻时第一次亲眼目睹,
还是很受触动。我对系统编制内这种一眼可以望穿未来的生活,顿生“绝望”。
待在“中房”不是我长久之计,
我已暗下决心。
1998年,在公司倒闭的三年前,
“人挪活,树挪去世”,
天下这么大,
自己该当出去走走的想法愈加强烈。
“时不我待”,
我决定去深圳闯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