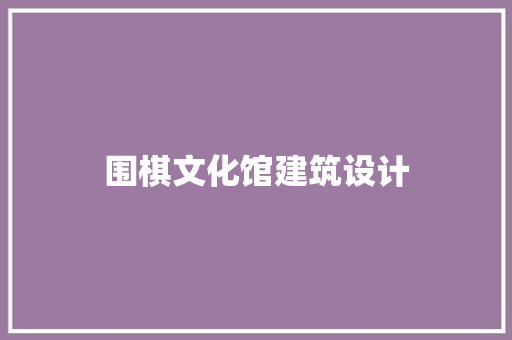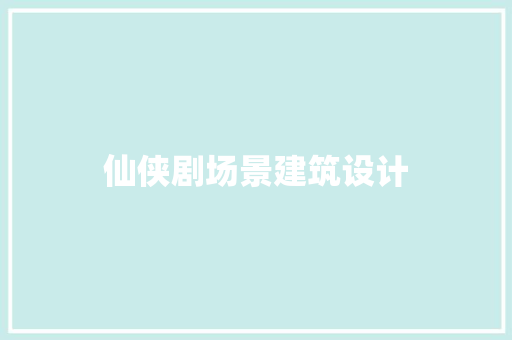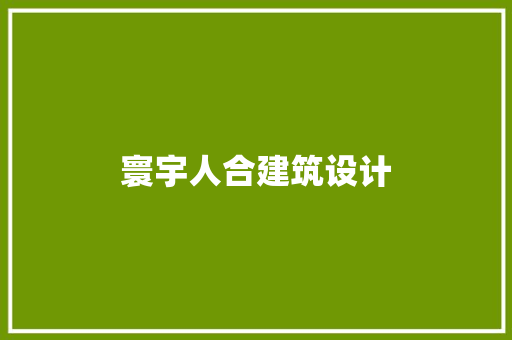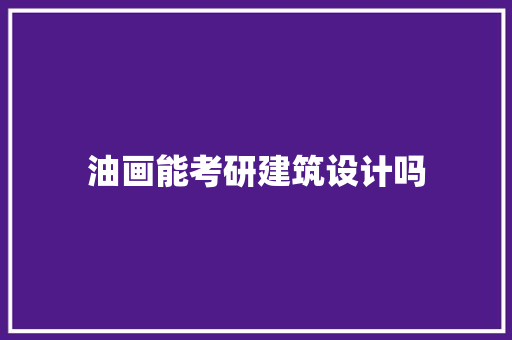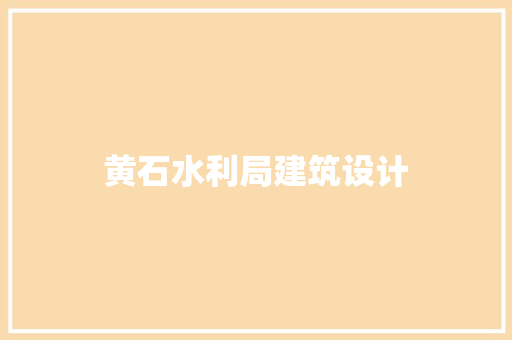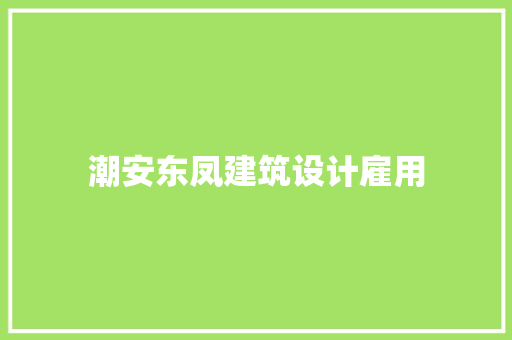运动会上的跳高比赛。
一户会宁人家在中堂挂的对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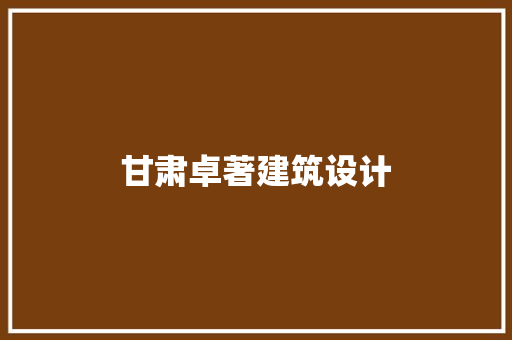
孩子们假期边放牛边读书。
地理教室。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我是带着好奇去会宁县的。
在此之前,作为在甘肃另一座小县城念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人,我听过这个地方的很多“传说”:
我的老师在教室上举例,会宁有老师在黑板两侧挂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见告学生,你考上大学了穿皮鞋当城里人,考不上就穿草鞋回屯子。
父母责怪我不足用功:“你便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人家会宁娃娃没水喝、没饭吃,一个个下苦学,都考到北京去了,北京都有一条会宁街呢。”
只管我的家乡离会宁县城还有700多里,北京更是在数千里之外,但大人们肯定的语气,让我一度以为,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能读书、能吃苦以及穷,成为会宁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会宁一中,成为回应我好奇的一个切口。在县级中学普遍“塌陷”时,这所中学在去年被列入甘肃的“卓越高中培植方案”。学校也曾收到北大、清华等名校校庆的喜报,感谢中学为大学培养了精彩的校友。
校长张贵荣答应了我的采访,他说,可以在学校随便看。
一
我到的那天是寒假结束后的开学日,一个高中生给我指了一中的方向,她有点遗憾地说,她没考上一中,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要623.5分,她所在的学校只须要500多分。
出租车司机得知我要去一中,说一中很好,他的小舅子便是一中毕业的,后来考上了大学,留在兰州当了干部。接着又说他是回族,一中在2018年、2021年都有回族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创造了历史”“攒劲的很!
”司机后来又自嘲,“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不知道咋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
会宁一中看上去和大多数县城中学没有两样,但也有些许不同——新修的校门右侧有一件浮雕,写着“仁义礼智信”。再往里看,有两座雕塑,一个是抽象派的,类似双手托举出希望,下面写着“人文日新”;还有一个是写实派的,孔子像。
在清华的大礼堂里也高悬着一块写有“人文日新”的匾额。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徐葆耕曾撰文:“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诲的灵魂和根本。日月牙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期间,都照耀着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肃静不致坠落;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该当学习一技之长,更该当学会若何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张贵荣说了类似的话,他希望会宁一中的孩子在搞好成绩之外,有艺术特长、体育技能,到了大学里,仍旧是一个佼佼者,到了社会中,还是一个生动的、精良的人。
考虑到会宁县在2020年年底才脱贫的实际,我以为这样的想法或许只能勾留在“想”的层面。
“掉队是全面的。”我读研究生时,一位教授感叹东西部差距时用过这样的句子。
二
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素有“秦陇锁匙”之称的会宁县,很多人家在中堂挂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
步入县里专门修的会宁教诲展馆,劈面便是1位老师带着4逻辑学生的雕塑,背后是一件意为“硕果累累”的浮雕。这里展示了自明朝洪武六年至2010年间影响会宁教诲发展的大事。
有图片资料显示:出嫁的女孩在裙摆上绣上状元出行图,寓意孩子往后考状元;不识字的老奶奶瞥见散在地上的字纸也会捡起来塞进墙缝里,由于“有字的纸不能被人踩”。上世纪50年代,时任会宁县长的冯琯或步辇儿,或骑驴,顶风冒雨奔波,整顿学校、修缮房屋、安排校长,乃至在每一位西席的任命书上亲自具名。还有供出3个大学生的单亲妈妈;背着干粮蹚水上学的兄弟俩;放驴时,挤在一起读书的小伙伴……
这是穷山沟,2020年第一季度,会宁县人均GDP仅0.28万元,在白银市垫底。但再穷不能穷教诲,2017年起,会宁县引进免费师范生,有不少于20万元的住房和生活补贴。
县教诲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自规复高考以来,该县已向全国运送大学生13万多人,个中,得到博士学位的1500多人、硕士学位的60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149人。
由于教诲,很多人的命运像县里流淌的祖厉河一样转弯。一位会宁人回顾,他的父亲和五叔分别是村落庄西席和村落庄年夜夫,他们“在那个时期家乡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
会宁一中西席王国良在1980年考上大专。他记得很清楚,那年,会宁全县只出了56个大学生,他是他们村落里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规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拿到关照书后,“走在路上,社员议论(他)”“亲戚挨个上门”“父亲的腰板也直起来了”。
有人开玩笑叫他“国家干部”,更实在的是,在大学校园里,他每个月能领到19元6角的生活费,还有6元的奖学金、4元的医疗费。“当时,一个化工厂的工人每个月才拿22元5角的人为。”王国良说。
在大学,花3角钱就能吃一份肘子,1角5分钱就能吃到番茄炒鸡蛋。而以前,除非夏天热狠了,王国良的父亲才会在集上买几个洋柿子(番茄),让他们兄弟姊妹解解渴。
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成为“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王国良说,他打头上了大学后,第二年村落里就出了两个大学生,个中一个还考上了兰州大学。
“通过读书有所作为,让家人不再那么辛劳是我读书的动力。”2020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刘佳维说。她家里有9口人,家庭收入全靠父亲外出打工。
前些年,有些家庭为了孩子上高中,荒着农田不管,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去县城陪读,涌现了“因教致贫”征象。
三
王国良在会宁一中执教30多年来,没有听过皮鞋和草鞋的故事。一次,去周边学校参不雅观,他看到教室里贴着“要想生富贵,需下去世功夫”的宣扬语,还以为有点夸年夜。
会宁一中的教室里,也有学生贴的标语:“每天六问”——问自己是否学懂弄懂,是否充分利用了韶光,是否不遗余力,是否有所收成,问老师问题了吗,高考目标是什么?
校园里,有人会站在学校大门附近的几棵槐树下晨读、晚读。有老师这样鼓励学生:高中三年固定在一棵树下背书。“有可能以前某个状元便是在这棵树下读书的,我们也要认定一棵树,好好学习,争取超过他。”
教室里后排摆着空桌椅,学生累了,去那儿站一下子、坐一下子。教室门外也有空桌椅,除了让学生解乏,老师也会在晚自习时坐在那里,一对一为学生解疑答惑。
这两年学校看重学生自学,老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薄弱点进行专项辅导,“之前是把一个班当一个人教,现在是把一个人当一个班教”。
在午休结束后,一些孩子会主动到讲台,给其他同学讲“逐日一题”。“给别人完全地讲下来,自己的提升更大。”高二宏志班的张馨丹说,这是自发的,谁对这道题的把握更好,谁就上去讲,有时候会有争议,同学们就一起谈论,直至将一道题延伸至一类题、一种有效的解题思路。
走在县城,看不到一家学科辅导机构。县教诲局一位事情职员笃定地见告我,哪怕在“双减”前,会宁县都没有一所学科类的辅导机构。这样的机构在会宁县活不下去,在学校学就够了。
张贵荣见告我,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甘肃每一个县都留招生老师的电话,唯独会宁县没有。家长以为,去省城读高中,赶不上在家乡读书。
“苦”学带来的不止一壁——一些学生也会因此产生较大的生理包袱。
如今也是一名高中西席的校友王乐天就曾在日记里给自己戴上“桎梏”——“想想我贫穷可怜的父母,想想我因贫辍学的弟弟,我没有情由挥霍光阴。从本日起,我要武断信念,努力学习,猖獗阅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请老天爷监督!
”
王乐天是背着舅妈上高中时用过的木箱和石油炉子,扛着铺盖卷来到会宁一中的,吃的是母亲优先留给他的白面。这些“厚望”,使得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创造自己的短板是“文综”后,高考前的那个寒假,他买了35套文综仿照题。每天五更,听到家里的花公鸡打鸣后,就趴在被窝里开始做题,每天一套,整整35天。他的双肘磨出老茧,至今还有痕迹。
做题的成效凸显出来,高三第二学期,王乐天的文综成绩从152分提升到了182分、202分、222分。为此,他还把“2”当成了自己命中的吉数。
2002年高考,作为高考改革后“3+综合”模式的第一次考试,王乐天吃了败仗,他的文综仅仅考了150多分。他倒在床上,3天没有用饭。
另一位85后的会宁学子有着类似的感想熏染,他直言,读书不只为自己学,还为父母学,考不好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对教诲太执着了,随意马虎把高考当成唯一一条路,韶光长了,一点挫折都会成为压去世人的稻草。”
这个担子永劫光压在了他的心里,即便后来他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事情,但在“梦想实现的中途”,总以为“欠别人太多,有放不下的人”。他又回到了会宁。
毕业后考入军校的张金峰说,特定时代条件下,“会宁教诲纯粹的‘去世学苦学’带给会宁学子根子里的固执和与大环境的扞格难入”。
他说,自己身边大部分会宁的老乡,每次一听大家说去KTV唱歌,就害怕,“用会宁传统的不雅观念看,学生就要齐心专心学习,而不是去唱歌舞蹈”。
他至今记得,为了他和他哥读书,初中时,父母把电视送给了亲戚,他高考结束后,才又买了电视机。
还有一位毕业生说,他读高中时,最怕父亲瞪他,“哪怕就一眼,也是一种生理、生理的双重碾轧”。
“读名校”一度成为会宁学子的“迷信”。王国良记得,自己班上有学生是全校前10,考上中国地质大学,但还想着复读,考清北。几个老师轮流动员,才把这逻辑学生说服。到了象牙塔,这逻辑学生总是寄来长达六七页的书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但4年后,他还是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
进入大学后,一些会宁学子会陷入不善交际、知识面较窄、创新能力不敷的“掉队”局势。
2015年,从会宁一中考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法学后,裴慧慧有过这样手足无措的时候,她说,专业课会设仿照法庭,要仿照辩解方、公诉方,大一时,她总会在分组的时候说,“我能不能光写辩解词,交给其他的同学去说”。
知乎上,有从前在会宁一中就读过的学生,匿名写下“讨厌会宁一中”的辞吐——“我现在不喜好再跟以前一样满口废话叽叽喳喳,也不喜好参加任何集体活动,并且不会跟很多人一样一提及高中就满满的幸福”。
让他产生伤痛的源头也是一件小事,一次考试,他没带腕表,估错了韶光,在间隔交卷还有10分钟时,理综卷子里的化学科目还没有作答,班主任很愤怒,认为这是一种挑衅,撕掉了他的卷子。
以前的教诲办法,可能培养出了一批应试高手,这是当地在创造“高考神话”时隐蔽掉的另一壁。
我也有过这样一直刷题,同时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会让父母蒙羞的时候。后果在我考完高考、离开县城后逐渐显现——父母想让我考师范,毕业后当老师,我由于分数不足去了师范学校的新闻系,但在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我对未来是茫然的。包括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代价判断会来源于外界对我的评判——我是否符合了家庭对我的期待,社会对我的期待。
“没有太大的压力,也没有过多的动力,对自己不理解、对生活没主见、对命运无选择。间歇性犹豫满志然后又连续做着短视的选择,沉迷于面前的安逸”,张金峰也有这样的担忧,他以为,如果一贯这样,考大学、事情、买房、结婚、在一座城市扎根,“最多也便是可以生活,谈不上造诣”。
四
“如果孩子只是一个读书人,不是一个社会人,那他不是人才。”张贵荣认识到问题所在。
在一所村落庄中学当校永劫,一位历史西席见告他,班上有个学生能把历史书从头背到末了一个字,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历史考得相称不理想。从那时起,他就在思考,老师要若何改变教室,学生要若何把书本知识灵巧运用。
后来,他成为会宁县教诲局副局长,分管全县教诲传授教化事情,还去了东部很多教诲发达地区参不雅观。
“东部的传授教化举动步伐和手段比较前辈,为学生供应了更好和更高的平台。”张贵荣还把稳到,东部的西席会设计自己专业发展的路线图,会主动进行校本教研,开展团队互助;教室也有很多新花样,看重突出学生的主体浸染。而彼时,会宁的西席还比较传统。
2012年调任会宁一中校长后,张贵荣决定成为“改革者”,将震荡到自己的东西带到学校——让学生学习辛劳,但不痛楚。
他想办一所有温度、宽度、高度的学校。他说,教诲要有宽度,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仅盯高考,“以分数论英雄”,“只抓成绩难有好的成绩”。教诲也要有高度,对学生的培养标准不局限在县城,要对标国家教诲改革发展中最新的哀求。
这些“宽高”提及来随意马虎,落实在传授教化的缝隙里很难。从开始,他就明白,如果靠行政命令去推动,改革只能短命。学校要先改变西席的“教”,再改变学生的“学”。
他记得,有一位物理西席,上课很负责,传授教化能力和水平也很高,但是传授教化成绩上不去,后来该西席试着自己只管即便少讲、让学生多做,教室果真面貌一新。
学校将原来45分钟的一节课变成40分钟,“留给学生互助互换磋商的韶光一点儿都不能压,反过来倒逼老师备课、讲课时更加精髓精辟。”
学校给西席留韶光,不能以为某个西席不成,就不去搭建发展平台,就一棍子打去世,“由于这个老师废掉了,就废掉了这一届的学生,乃至是几届、十几届学生。”
很多东部学校来这个不塌陷的县中稽核。有西席创造,这个穷山沟教诲很有活力,这里的西席流动性不大,也没有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西席90%都是会宁籍,对当地教诲很深情,很“主人翁”。
一位福建南平市的西席表示,“校长就该当像年夜夫那样,为学校的每一天‘诊断’,也要帮助每一个教职工‘诊断’,使学校在这种和谐的诊断中创造‘病灶’,并在自我的反思与管理者的做事中自我病愈。”
五
不止一位会宁一中中层领导见告我,自己宁肯不办法导职务,也要当班主任。
陈海龙便是个中一员。他对外校一位西席提出的“夸夸法”感兴趣。那位老师提到,他的婚礼从主持到证婚人再到伴郎都是学生客串的,这让他很倾慕。
“办婚礼做不到了。”陈海龙说,他把这套“海夸”用到了传授教化中——学习差了夸同学字好,字写得差了就夸同学完胜利课态度负责。
班里一位同学由于沉迷看小说,成绩退步,他在批评即将脱口而出时选择了“刹车”,反而用一套《大秦帝国》和学生打起了赌,许诺他,高三毕业后能考入自己空想的大学,就把这套书送给学生。“强人要有强大的意志,要会选择”,他以为,这本书能见告学生这个道理。
教导处主任温振堂现在还带语文课。学生说他“如深潭是温,似高山是振,元气满满传染他人是堂”。温振堂谦逊,以为这是学生有才。他的桌子上,有一本放开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春天夜晚里,他也会主动提起郁达夫《东风沉醉的夜晚》。
他鼓励学生读报纸、朗诵,提出不同见地,高三总复习时,他也让学生去思考命题人的思路、相互点评同学们的不雅观点意见。
年轻西席马英英研究生毕业于中南大学,去过斯坦福等多所大学互换,履历俊秀。
她创造,哪怕她教的宏志班有全体学校成绩最好的孩子,但大家还是有点儿怕说英语。她挨个儿鼓励,给每个人发了她设计的奖牌。
她传授教化生盛行的课桌舞,带着学生读英文原版小说、英文报纸,探究英语学习方法,协力完成一本英语学习条记……省里组织“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系列展演活动,头年,没人参加,第二年,学生乐意参赛,她又兴冲冲排练了一台话剧。比赛后,她带着孩子们去庆祝,吃火锅、玩密室逃脱……
逐渐地,孩子们不再畏惧英语,他们看用英语讲授的物理课视频、谈论时下的新闻热点,前不久,还由于两会有代表委员提出“网络游戏该当对未成年人全面禁止”,她组织了一场小型辩论赛,大家同等认为,这个建言没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实际需求。好玩的是,课上要学萧伯纳的《卖花女》,一些男孩子争先恐后要去反串这个角色。
马英英也在这个过程中感想熏染着作为老师的“幸福感”,学生亲近她,一下子叫她“领头羊”,一下子又叫她“新世纪的啄木鸟”,还戏称她是 “爱因斯坦”,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喊她“英子姐”“老英”……
一次,班上的英语没考好,班里有同学给西席写了一封古文道歉信。信的末了是,“吾辈必能以此为戒,因矢于师长西席: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而改之,是谓进矣。学生必进,岂无过焉。既往不咎,未来可期。”
马英英在假期里没有支配作业。这也是她的传授教化风格,她以为假期便是玩,放松,开阔眼界。
开学后,孩子们都带来了自己总结的英文条记。
“现在,我们的学生明白了,即便没有给出选择,他们的人生也可以豪华定制。”马英英说。
六
“老师发展为完备的老师,孩子离发展为完备的人的目标会更近。”张贵荣说。
老师努力让四周的山峰不限定孩子们的视野。高一新生入学,要在“体育、艺术”两大类10多门校本课程中选课,同时,至少加入一个社团,培养一个“特长”。一位地理西席平时喜好跳拉丁舞,办起了拉丁舞社团;一位政治西席,附近退休本该“躺平”,却在书法社团里挑起了大梁。
美术西席马伟斌上素描课,他编了一本校本教材。考虑到学生并非“美术生”,他对教材里的内容多次筛选,将常涌现的16个石膏体简化成正方体、圆柱还有球体,“韶光有限,既然要学就学最精华的部分。”马伟斌阐明,这三个石膏体险些能组成其他所有的石膏体。
玩并没有延误学生学习。体育西席任海亚至今与2015级足球队的学生保持着联系,那是他进入会宁一中后带的第一支足球队——18个学生,10人考上了研究生,还有3人读到了博士。
学校的硬件不算好,社团有些简陋,教具、器材大多来自捐赠。航模社团的辅导老师李重君说,刚学航模时,他不敢飞,由于这些都是西部的部队给学校捐的,大飞机一个好几千元,怕弄坏,只能反复在网上找教程,买一些便宜的模型来组装、试飞。
电子掌握技能社团的一些元器件也要从学校淘汰的旧电脑上拆。但这些仍旧在学生身上播撒着科学精神的种子。
梁开彦曾是这个社团的,高二有大半个学期,每个课间都会跑去社团做收音机,一遍遍走线、一遍遍焊接,直到收音机吸收到电台旗子暗记。他还在收音机背面焊上了会宁一中和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后来上了大学,他研究汽车灯光的自动转化。如今,他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从事智能家居研发。
七
穿行东西部学校的张贵荣说,会宁一中不怕与周边任何一个县的县中去比较,乃至也不怕和全国的县中比。
在这个梁峁起伏、沟壑纵横,自然环境不优胜,常驻人口约50万的县城,学校连续9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在5人以上,二本上线率在2021年达到98%。
“教诲质量不即是分数,但分数是见证教诲质量的一部分。老百姓也会从这个角度去评判教诲。”张贵荣说,现在,他不担心成绩,也有好几年韶光,不在校门口张贴红榜。他担心的只是没有正常发挥的孩子。
附近高考,5月槐花飘喷鼻香,高三学生不搞“临阵磨刀”,他们办文化节、科技节、生理节,这个时候,最主要的是让学生调度心态,把大考当平常考。功夫到了,瓜就熟了,“学习是12年的一个结果,不是几个月就能把成绩提上去的”。
学校也洞开校门办学。上海曹杨二中的孩子来这里研学,与会宁的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贵州省麻江县第一中学学生也来学习,学他们穷则思变,坚韧朴实。
这些西部“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也让东部的孩子吃惊,他们冲破了会宁人“苦学去世学”的刻板印象。张馨丹此前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3天研学活动,她全程参与全英文传授教化。
她们小组的谈论话题是环保,刚开始,她向马英英求救,马英英谢绝了她美化句子、纠正发音一类的要求。终极,张馨丹与其他小伙伴完成了“生物多样性”观点的阐释,拿到了不错的分数。
16岁的李宁常常和父亲一起组装航模。在动手过程中,父亲越来越多地看到孩子身上的品质,他改变了自己的教诲思路,不一定要考多好的大学,而是希望儿子发展为有主见、能拼搏的人。
希望往后学习信息技能的张婷喜好画画,她说,哪怕是和相对呆板的技能打交道,也要在心里保留一份浪漫,“就像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创作,画完之后,这张纸就有了代价。”
受邀参加清华大学校庆时,张贵荣创造,清华学生科协的副主席是会宁一中的学生,山沟沟的孩子不是只会刷题。
八
还有一些“成绩”和成绩无关。一位叫“焦焦”的校友,从2019年参加事情以来,每年帮助3名毕业生每人300元的上学车费。不同于其他毕业于名校的校友,焦焦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施工员。他说,这个动机是在2014年学校举办的成人礼上产生的。
校警“伏叔”顶着大雪清扫校园的身影被发到了学生“槐花飘喷鼻香”的视频号里,不少学生为他点了赞。有一条留言说:“每一年无论秋日的落叶还是冬天的大雪,一中校门前的槐树下总有伏叔挥舞扫把的身影,扫把摩擦地面沙沙的声音,大概是一中除了书声外最美的声音……”
伏叔回应了满屏的温暖,他说希望孩子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然后学成归来之时对我说一声:“伏叔,我回来了”。
张金峰说了语义靠近的话。我们终极将此归结为一个教诲快慢的问题——在要快速提成绩的那个韶光段,我们想着考高分,却很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到了社会上,我们的发展是比较慢的。而现在,从一开始孩子们有自己的代价不雅观、人生不雅观,他到社会上去,走得是要比同龄人更快的。
采访了一圈下来,我开始有些理解会宁县中征象——放在资源、见识、制度、经济和发达地区都不是一个维度的现实下,一个普通孩子要改变命运,大概真的只有去放弃一些东西,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得到参与社会洗牌的一次机会。
有人评价,能从穷苦中奋斗出去的他们,已经有能力有思想准备面对更大的贫富差距,然后改变。
一开始不敢发言的裴慧慧也在大学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逐步走向台前。本科毕业后,她在南京的一个区法院事情过一年韶光,还在兰州一家律所考试测验过做状师。之后,又报考了研究生。
偶尔,她会倾慕弟弟,这个00后还有70多天参加高考,他会吹萨克斯,很明确自己要考什么学校。
但裴慧慧以为,自己的路也没有白走,“前面有一个人替你走过不少弯路之后,剩下的那个人肯定会有不少坦途”。
到了北京后,我创造北京根本没有会宁街,那不过是大人骗小孩读书的谎话,但想想那么多从会宁考到北京的学子,这条街又彷佛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