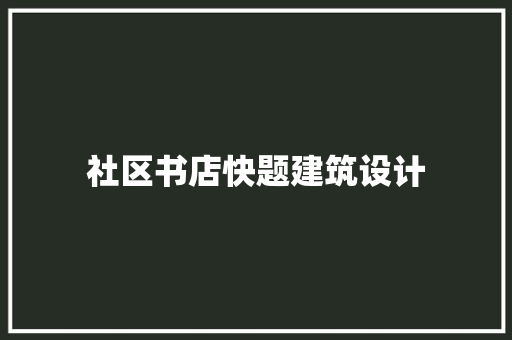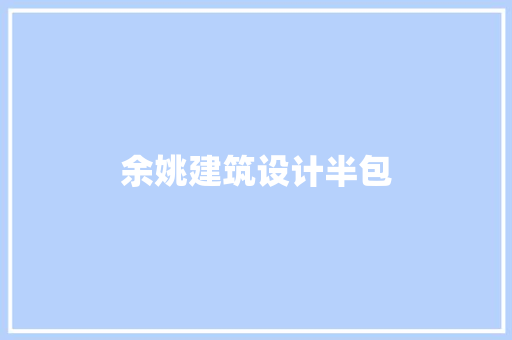在很永劫光里,陈安栋给人一种“低调”的印象。
如今,间隔他得到第二届新观点作文大赛一等奖已经十七年了,间隔他的处女作《高三四兄弟》的出版也十六年了。

“年纪越大越精确,越快乐。”10月20日,一身笔挺西装、扎着一戳小辫的陈安栋接管澎湃新闻专访。面前的陈安栋不再是那个休学一年去西藏思考人生的大学生,也不再是那个自诩“宇宙第一才子”、“速写线条可以和罗丹比较”的热血青年。他开了一家CHR建筑事务所,新出的作品也无关小说,是一部哲学思辨小书《我知道?》。
陈安栋,背景为他设计的玻璃砖墙。
反思自身所拥有的文化
翻开《我知道?》的目录,映入眼帘的是“福柯之笑、道、笛卡儿之‘我思’、列维纳斯的他者......”陈安栋说:“这是本丢脸的书,我给它打八十分吧(满分一百)。”
小书出身于陈安栋在巴黎马拉盖建筑学院一次例行陈述时所面临的窘迫。那天,当他将位于巴黎北部的某个区域描述为“这是一片低矮的贫民窟”时,他吃惊地创造同学们完备茫然于这个平淡无奇的句子,并随即展开了各种提问:为什么这是“一片”而不是一块?为什么说它是“低矮”的?为什么称它是“贫民窟”?有什么凭据吗?
“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在支撑着我的那句话,我只能说是一种觉得。”在领教了法语和法国人思维的精确性后,陈安栋产生了对汉语以及中国人模棱两可的思维的兴趣。
“我开始反思我的自身和我所拥有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里,统统彷佛本该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不会去想这句话有没有证据、是不是事实,我们很难区分主不雅观和客不雅观之间的那条界线。”于是,就有了陈安栋在书中的思考。
“这种 ‘自说自话’的特色,我以为首先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创造力,限定了国人的履历拓展。”陈安栋见告澎湃新闻,我们的履历永久是已经存在的履历,一旦分开了履历就感到恐怖,不愿知道现实是什么。“其次,在美学上也会有问题。我是建筑师,从建筑角度来看我就创造中国的 ‘空间’一贯在一个范式中发展,几千年也没有很多新的空间履历。当然园林也很美,但它实在是根据先在的视觉形象复制的。”
陈安栋的家,他返国后改造设计的第一个屋子。
“再比如,我对科学比较欣赏的定义是——科学不是永久对的,科学的容错性是很强的。比如我们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就会说‘这个科学无法阐明’。如果我们的‘科学’,比如五行,总有一种强大的阐明力,总可以自作掩饰回应任何问题,那么肯定不是科学。”陈安栋说,“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是一体的,苏格拉底从一开始就说你知道的都是不对的,而我唯一知道的便是我一无所知。科学要承认——我不知道。”
在他看来,“自说自话”有好有坏。“好处是履历永久不会消逝,坏处是我们缺少对这个宇宙的兴趣。我们不应该只是去想象这个天下,而是该当去看、去创造、去研究。”
实质上还是写小说的人
在《80后作家访谈录》中,陈安栋很早就流露出自己对哲学、逻辑与思考的着迷。
当别人问他:“你看过很多文学作品吧?”他直言:“不多。我更喜好看哲学,还有科学史。纯文学对我来说缺少思维上的乐趣,当然精品除外。”
现在也是如此。早上五六点是陈安栋的阅读韶光。“那个韶光点我特殊希望看到一些,像喝咖啡一样,能让脑筋转起来的东西。”陈安栋说,“我以为吸引我的还是想象力,但文学有时候想象力太弱了,只能想象出一种场景和故事,但想象不出一种逻辑,想象不出阿喀琉斯永久追不上一只乌龟这样的逻辑。这种思维本身的快乐,我以为小说里面比较少有。”
如果要他总结,哲学或思考是和建筑学比较相通的东西。“那是一个措辞化的东西,比如你画一堵墙可以画得很美,但当你叫工匠造出来的时候,就必须把细节逐一标清楚,否则工匠不知道怎么造。这就像你的思想和意识化形态,变成措辞时须要变得可以阐明、逻辑清晰,这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陈安栋和他的“贝多芬去世面相系列”。
“而小说是从模糊到模糊,或者从清晰到模糊的过程。小说能说清楚的话,我以为小说可能就没故意义了。以为有点什么,但又说不清楚,是我眼里小说比较空想的效果。”
如果是写作,陈安栋坦言还是更喜好写小说。“写作和阅读不一样。我以为我实质上还是写小说的人。写哲学太累了。我考试测验过很多事情,包括建筑、写小说、画画、练琴,但我以为没有比哲学思考更累的事情。写小说的话我就以为不应该是一种非常累的过程。小说会有很多飞跃的时候,让你腾云驾雾的时候,进入某些意境的时候,这些时候不会像哲学那样被措辞压着走,而是和措辞融为一体。再严明的、学术的小说,比如格非、卡夫卡那种,也会有很多快乐的时候。写哲学只能说是一种愉快,喝了很多杯咖啡的觉得,强烈却很重。”
近期,他刚完成了一篇名为《地球原来是个蛋》的中篇小说。“我自己以为写得很好,创造了一种我自己的措辞,而且构建出一种以前没有的履历范畴,可以带来一些新的空间体验和情绪体验。”陈安栋略得意地见告澎湃新闻,“我自己比较满意,如果别人看不来也没紧要。写东西关键自己要嗨,自己不OK的话那弗成。”
这让人想起多年前别人问他如果作品不揭橥是什么觉得,他的回答是:“很骄傲”,由于“一个东西不被揭橥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写得太差,一种是写得太好,这样就有百分五十的几率可能是精良了,再加上自傲,以是很骄傲。”
陈安栋正在设计的幼儿园
新观点的印记肯定是有的,只不过迢遥了
18岁那年,陈安栋得到了新观点作文大赛一等奖。
“这个事情已经由去好久了。但我不得不承认新观点肯定影响了我,不然我也不会去武大(保送),还得到了一个作者的身份。这种印记肯定是有的,只不过现在的状态和它比较迢遥了。”
和不少已成为职业作家的新观点获奖者比较,陈安栋低调且低产,《高三四兄弟》和《情爱胶囊》都已成了冷门出版物,很多人乃至不知道他转而成为了一名建筑师。
“为什么没有以写作为生呢?可能是由于我很害怕这件事情做到后来会和上班一样无聊,我对特殊喜好的事情都是敬而远之的。我现在就很愉快,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自己很嗨就行。”
那么对建筑这行呢?陈安栋笑言:“当然没那么爱了。我喜好建筑,但绝对不能说是挚爱。建筑是一个可以成为妻子的角色,你可以每天和它打仗也不会以为很烦。你和它感情很深,但也不会把爱不爱的放在嘴上。它是比较随意马虎日常化的,由于建筑里纯粹的创造时候并不是特殊多。做这行还有很多噜苏的事务,你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而且建构行为我从实质上便是反感的,我比较喜好解构和打碎。”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要靠它用饭的。社会生产是大的社会一环,没办法避免。”在陈安栋看来,小说一定不是一种生产行为。“小说是情人吧,而且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想找也可以不找,特殊远但是特殊好。它不会干涉你的生活。而且我以为小说只有这样才故意义。”
哲学思辨小书《我知道?》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时候,陈安栋以为建筑和哲学还有些相似——线条都是直的,并且精确到毫米。“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科学和精确。”
曾经的陈安栋可以一个人裹个大棉袄蹭着大卡车就去西藏,睡在地上不要紧,找别人蹭吃蹭喝也不要紧。他还以为自己什么都会,油画也会,钢琴也会,建筑也会,还懂哲学,切实其实是“宇宙第一才子”。
“回忆起来,以为当时自己便是很傻的那种人。现在假如再提宇宙第一才子,我只敢去网上取一个好玩的笔名了。”他说,“和过去比,我少了很多冲动和感性,肯定会遗憾的。但是也没办法,不可能又睿智又感性,这个平衡非常困难。”
“想若何就若何,那是一种,十八九岁的觉得。”但陈安栋对眼下的生活也觉得从容,“我对万事万物都挺有兴趣,包括植物学、昆虫标本啊。我想让自己在这个城市处于闲逛的状态,我以为自己是那种过着日复一日伟大生活的人。”